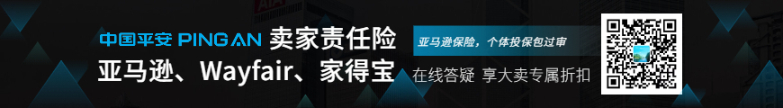它們就是是各大主打低價的“一元店”,當中的代表是Dollar General(達樂集團)和Dollar Tree(美元樹)、Five Below等。
圖/達樂的商店
其中,達樂和美元樹是經營了數十年的老牌零售商。
達樂成立于1939年,1968年就已經上市,如今市值272.24億美元,而美元樹成立于1986年,1995年上市,如今市值276.59億美元。
經營便宜商品的兩大零售商都上市了,說明美國下沉市場的空間很大。
這種便宜的“1美元店”在美國遍地開花,瞄準美國5環外的低消費市場。截2016年,美國就有3萬家線下“1美元店”。
達樂和美元樹在Temu進入之前風頭旺盛。
美國零售聯合會發布的《2023年美國零售商百強榜》顯示,達樂和美元樹在2022年以378.7億美元、279.1億美元的成績位居第17和20名。
然而,Temu橫空出世之后,天地變了樣。
Temu就像一個沒有師承的無名少年,一出江湖,以一套亂拳打傷一片老師傅。據Earnest Analytics的數據顯示,截至11月,Temu已經占據美國折扣零售類別約17%的市場份額。
此長而彼消,達樂和美元樹的市場份額雙雙下跌:達樂的市場份額從今年1月份的57%跌至11月份的43%,下降14個百分點,而美元樹則從32%跌至28%,下降4個百分點。
在Temu的猛攻之下,兩個折扣巨頭的股價也紛紛下跌。今年達樂的股價跌幅為50%,美元樹則跌了24%。
Earnest Analytics營銷主管Michel Maloof認為“Temu的消費品和家庭用品的價格較低,這給實體折扣店帶來了更大的威脅”。
市場份額和股價雙雙暴跌 ,達樂和美元樹應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痛感。
從這個角度上看,Temu雖然是線上零售平臺,但它先革掉的是美國線下零售平臺的命。
這主要是兩個原因:第一、同樣主打低價;第二、用戶畫像重疊度很高:今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報告描述了Temu的用戶畫像:62%女性、38%男性。年收入5萬美元以下占比55%。
關于用戶畫像的重疊,達樂集團的首席執行官托德·瓦索斯提供的數據成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證據。
瓦索斯在2017年接受采訪時描述過1元店的核心客戶:一、女性;二、雙收入家庭每年稅前收入4萬美元;三、工作穩定但工資增長起伏不定,她的可支配收入約為2%,即每年800美元;四、她對價格變化非常敏感;五、她可能擁有一部智能手機,但她可能沒有Amazon Prime。
沒有亞馬遜會員Amazon Prime,這是關鍵點,Amazon Prime會員費一年都要119美元,這是對于下沉消費人群來說,是一大筆開支。
對于這些下沉消費人群來說,很難理解,為何我一件商品都還沒有到手,卻要我先繳納119美元的年費?憑什么?
而在亞馬遜的用戶中,有相當大的比例購買了Amazon Prime會員服務,這意味著這部分用戶人群似是與“1美元店”的用戶有很大的區別。
Temu以超低價商品沖上美國市場時,必然對這部分用戶有很大的殺傷力。
不過,不可忽視的是,美國的中產階級的數量正在縮水。
Pew Research的數據顯示,從1971年到2015年,美國中等收入者所占總收入份額從61%降至50%。
根據人口普查局的數據,到2021年底,至少有3800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,這一數字占總人口的11.6%。
這些人可能會成為Temu的新用戶。這對于美國的各大1元店來說,都是一個挑戰。
Temu的成功,背靠的是中國的供應鏈。
但并不是所有賣家都愿意在Temu上銷售。
目前在Temu上銷售的賣家,大部分銷售的是那些“薄利多銷”的款式,而對于新開發的產品,一般不愿意去嘗試,此外,有相當一部分賣家是抱著清貨的態度去賣。
同時,入駐的賣家越來越多,競爭越來越激烈。Temu的買手時刻盯著1688等線上平臺,一旦監測到更低價,就要求賣家下降。
此外,Temu越來越不愿意貼錢了。
早期Temu是會承擔物流費、倉儲費等費用的,如今,隨著入駐賣家的增加,Temu收緊了政策,比如物流費,賣家也要承擔一半了。
隨著Temu手上握著的供應鏈資源越來越多,入駐的賣家也越來越多,可以預見,Temu各類政策都會收緊。其中,“同款比價+最低價上架”的機制將會越來越嚴厲,也將會傷到很多賣家。
卷低價的生意,并不是想象得那么好做。(億觀分析組)